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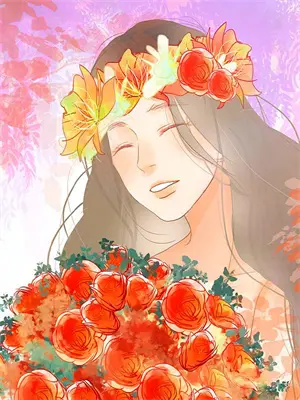
其它小说连载
书荒的小伙伴们看过来!这里有一本飘渺爱神的《退伍我杀了仇人全家》等着你们呢!本书的精彩内容:男女主角分别是飘渺爱神的男生生活,同人,虐文小说《退伍我杀了仇人全家由新锐作家“飘渺爱神”所故事情节跌宕起充满了悬念和惊本站阅读体验极欢迎大家阅读!本书共计124951章更新日期为2025-10-15 19:00:13。该作品目前在本完小说详情介绍:退伍我杀了仇人全家
主角:佚名 更新:2025-10-15 19:36:39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本文根据张某某事件改编。。。秦巴山腹地·黑水沟村寒风像淬毒的刀子,
刮过光秃秃的山梁。十六岁的陈小山背着高过他头顶的柴捆,
每一步都在冻硬的泥地上踩出咯吱的裂响。柴刺扎进他单薄的棉袄,
肩胛骨的位置早已磨出血痂,混着汗,结成一板暗红的硬壳。这点疼算不得什么,
他心里的那道口子,才叫真正的血肉模糊。转过山坳,家的土坯房映入眼帘。
可他的目光却像被烙铁烫到般猛地缩回——隔壁那栋簇新的、贴着白瓷砖的二层小楼,
在灰扑扑的山坳里刺目得如同一个流脓的疮疤。那是王家的新宅。
红砖墙在暮色里泛着暗沉的光,像凝固的血块。三年前,也是这样的腊月天。
为了一垄不过两尺宽的菜地,王宝田和他刚满十八的儿子王金龙,
挥舞着铁锹和顶门杠冲进陈家的小院。母亲王秀娥,那个说话都不敢高声的女人,
只是张开手臂护住身后吓傻的小山,像护崽的母鸡。混乱中,王金龙手里的顶门杠带着风声,
狠狠砸在母亲的太阳穴上。“噗——”那是小山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声音。沉闷,短促,
像熟透的西瓜被砸裂。温热的液体溅了他满脸,浓重的铁锈味瞬间塞满鼻腔。不是汗,是血。
母亲的血。她甚至没来得及哼一声,就像一捆被砍断的麦秆,直挺挺地倒在他脚边。
眼睛还睁着,映着灰蒙蒙的天,里面盛满了小山看不懂的惊愕和一种……未尽的牵挂。
“娘——!”少年的嘶吼劈开了山村的死寂。后来?后来是漫长的扯皮、推诿。
王家人咬死了是“互殴”,是陈秀娥“自己撞上来的”。
法医报告上冰冷的术语写着“重度颅脑损伤致死”,
可判决书上更冰冷的字眼是“防卫过当”、“激情犯罪”。王金龙,
那个用顶门杠敲碎母亲头颅的凶手,只判了七年。王宝田,毫发无伤。而陈家的顶梁柱,
没了。“七年…七年啊…” 父亲陈老栓佝偻在灶膛前,
灶里微弱的火苗映着他一夜之间全白的头发和沟壑纵横的脸。
他手里捏着那份早已被摩挲得卷边发黑的判决书复印件,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声音像破风箱在拉,“一条人命…就值七年…金龙那崽子,
在里头还能减刑…这世道…这世道哪还有咱穷人的活路!” 他猛地咳起来,咳得撕心裂肺,
咳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狠狠啐进火里,发出滋啦一声轻响,瞬间化为青烟。
小山沉默地往灶里添柴。火光跳跃,在他脸上投下明暗不定的阴影。他盯着那簇火,
看到的却是母亲倒下的身影,是王金龙被法警带走时回头瞥来的那一眼——没有愧疚,
只有一种混着轻蔑和“算你走运”的冰冷。那一眼,像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了小山的心尖上。“爹,吃饭。”小山把一碗几乎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放在父亲面前。
桌上只有一小碟咸得发苦的萝卜干,
还有三个供在母亲褪色遗像前的、冻得梆硬的窝窝头——那是家里仅有的细粮。
陈老栓没动筷子,浑浊的眼睛盯着遗像:“小山…过了年,
你跟我去山外头吧…这地方…脏了咱的眼,寒了咱的心…”小山没吭声。他走到墙角,
那里堆着母亲出事那天穿的血衣。父亲一直不让洗,也不让扔,就用块破塑料布盖着。
小山掀开塑料布,一股淡淡的、混合着泥土和铁锈的陈腐血腥味立刻钻入鼻腔。他伸出手,
指尖小心翼翼地拂过衣襟上那片早已变成黑褐色的、硬邦邦的血渍。那血渍的形状,
像一个咧着嘴无声嘲笑他的鬼脸。恨意,像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绕住他的心脏,越收越紧,
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这血,是母亲的血!这恨,是刻进骨头缝里的!
屋外突然传来王家院子里放肆的笑闹声,夹杂着王金龙弟弟炫耀的声音:“哥来信了!
说在里头表现好,管教夸他呢!说不定能再减刑!” 接着是王宝田得意的大嗓门:“那是!
我王家的种,到哪都出息!”“哐当!” 小山手里的柴火棍狠狠砸在地上,断成两截。
他猛地冲出屋门,像一头被激怒的小兽,赤红着眼睛冲到王家那崭新的、刷着红漆的大门前。
新贴的春联刺着他的眼——“吉祥如意”,“家宅平安”。平安?如意?
他们凭什么平安如意!“啊——!” 少年压抑了整整三年的悲愤、屈辱和不甘,
终于冲破了喉咙,化作一声凄厉到变调的嘶吼,在山谷里久久回荡。他抬起脚,
用尽全身力气狠狠踹在那扇象征着王家“平安如意”的红漆大门上!“咚!” 一声闷响,
门板纹丝不动,只震落了些许灰尘。巨大的反作用力震得小山踉跄后退,脚踝传来钻心的疼。
可这疼,远不及心头的万分之一。王家的狗狂吠起来,窗户里探出几张惊愕又带着鄙夷的脸。
小山死死盯着那扇门,胸膛剧烈起伏,嘴唇被自己咬出了血,咸腥味在嘴里弥漫开。
他缓缓弯下腰,从冰冷的泥地上抓起一把混着碎石和枯草的泥土。这土里,
有母亲倒下的地方渗进去的血,洗不净,化不开。他紧紧攥着这把冰冷的“血土”,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直到泥土从指缝里渗出。他转过身,不再看王家灯火通明的新房。
一步一步,拖着那条疼痛的腿,走回自家那间低矮、破败、弥漫着绝望和药味的土坯房。
每一步,都在冻土上留下一个沉重的脚印。灶膛的火快熄了,屋里一片昏暗。
陈老栓蜷在炕角,发出压抑的、像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小山走到水缸边,
舀起一瓢刺骨的冰水,劈头盖脸浇在自己头上。冷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冻得他浑身一激灵。
他抬起头,水珠顺着额发滴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昏暗的光线里,少年的眼神变了。
那里面不再有泪,不再有茫然,只剩下一种近乎死寂的冰冷,
和一种比秦巴山最深处的寒冰还要坚硬的决心。那恨意,不再是灼热的火焰,
而是沉入了骨髓,凝成了寒铁。他看着水缸里自己扭曲的倒影,嘴唇无声地翕动,
吐出三个字,轻得像叹息,却带着斩断一切的决绝:“我,记,着。”窗外,
王家新房的灯光,像一只嘲弄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陈家这片浸透了血泪的黑暗。
而少年陈小山心中那座名为“复仇”的冰山,在母亲温热的血和父亲绝望的泪水中,
在司法冰冷的“公正”和王家刺目的“平安”映照下,轰然拔地而起,再无消融的可能。
这把“血土”,从此牢牢攥在了他的命运里。山子在南方五金厂落下脚。流水线咬碎昼夜,
机油味渗进骨髓。他总在深夜惊醒,掌心残留母亲后脑温热的触感。工友老赵是退伍兵,
看他沉默得像个影子,便常拉他喝酒:“心里有洞,得拿光去填,别拿刀子。
”山子只是磨着手里的弹簧钢片,金属冷光映着他眼底的冻土:“光…照不进我那座山。”。
。。。。。1999年冬,南方某野战军侦察连驻地。寒风卷着操场的沙尘,
抽打在脸上像细密的针。新兵陈小山——现在所有人都叫他 山子 ——站在队列里,
背挺得笔直,像一杆插进冻土里的标枪。三年的五金厂生涯,油污浸透了他的指缝,
却没能磨灭他眼底那簇冰冷的火。军营,是他主动选择的熔炉,
他要在这里把自己锻成一把真正的、能劈开黑暗的刀。
四十公斤的全副武装越野是侦察兵的日常。别人咬牙硬撑,山子却像不知疲倦的骡子。
每次跑到最后两公里,肺叶火烧火燎,小腿肌肉突突直跳,眼前阵阵发黑。他眼前浮现的,
是母亲倒下的身影,是父亲咳出的血沫。那画面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灵魂都在尖叫,
反而逼出骨缝里最后一丝力气。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在背包里多塞两块砖头,跑在队伍最前面。
当终点线在望,他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冲过终点后直接栽倒在地,呕吐物混着血丝,
却死死攥着胸前代表第一名的红旗布条。练据枪,枪管上挂水壶,肘部悬砖头,
一趴就是两小时。汗水流进眼睛,沙地硌得骨头生疼,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山子纹丝不动,
眼神透过缺口准星,死死锁定百米外的半身靶。
靶心在他眼里幻化成王金龙那张模糊又狰狞的脸。他呼吸绵长,手指稳得如同焊在扳机上。
汗水在他身下洇出一个人形的深色印记。
班长张猛暗暗心惊:这小子眼里有股狼盯上猎物的光,狠得瘆人。
侦察连的格斗训练是真打实摔。山子瘦,但骨头硬得像铁。一次对抗,
他被一个壮硕的老兵锁喉压制,脸憋得紫红,眼球都凸了出来。
就在众人以为他要拍地认输时,他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嘶吼,
身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一个极其刁钻的“兔子蹬鹰”竟将老兵反摔出去!他翻身骑上,
拳头带着风声就要砸下,却在离老兵鼻尖一寸处硬生生停住,指关节捏得咔吧作响,
眼底的疯狂与克制激烈交锋。张猛冲上来拉开他,看到他手臂上被老兵指甲抓出的深深血痕,
山子却浑然不觉,只是死死盯着自己的拳头,仿佛在确认这力量是否足以撕碎真正的仇敌。
淬火的荣光: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堤坝告急。山子所在班负责堵一个巨大的管涌。
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杂物疯狂倒灌。沙袋扔下去瞬间就被冲走。情急之下,
山子吼了一声“跟我上!”第一个跳进齐胸深的激流中,用身体死死抵住沙袋墙。
冰冷刺骨的洪水冲击着他,水下的暗流像无数只手在撕扯。他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
牙齿咬得咯咯响,为战友筑墙争取了宝贵时间。上岸时,他冻得嘴唇乌紫,
小腿上被水下杂物划开的口子翻着皮肉,却一声没吭。驻地附近突发山火,火借风势,
直扑村庄。山子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面对冲天烈焰和呛人的浓烟,他顶着湿透的棉被,
一次次冲进火场背出被困的老人和孩子。眉毛头发被燎焦了,手臂上烫起一串水泡,
他浑然不顾。最危险的一次,他刚把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递出来,身后的房梁就轰然倒塌,
火星溅了他一身。战友们惊呼着把他拖出来,他抹了把脸上的黑灰,只问:“还有没有人?
”一次重要的演习前,蓝军在某关键路段设置了复杂的连环诡雷装置训练弹。
排除时间紧迫,稍有不慎就会“伤亡”并导致任务失败。排爆手尝试未果,气氛凝重。
山子仔细观察了爆炸物结构——那复杂的线路缠绕,
竟让他想起了五金厂里那些冰冷的机器齿轮。一种奇异的冷静笼罩了他。
他主动请战:“报告!我在厂里拆过比这更乱的电机线路!”在战友们屏息凝神的注视下,
他趴在地上,像最精密的仪器,用排爆剪小心翼翼地一根根剥离、判断、剪断。
汗水顺着他紧绷的下颌滴落在尘土里。当最后一根代表危险的“绊线”被剪断,
他长舒一口气,后背军装已被冷汗浸透。演习成功,他被授予“侦察兵尖子”称号。边境,
配合地方武警执行一次边境缉毒协查任务。毒贩异常凶悍,驾驶改装车辆疯狂冲卡。
山子所在的拦截小组车辆被撞翻。在翻滚的车厢里,他头部撞伤,鲜血糊住了一只眼睛。
但车辆停下瞬间,他竟第一个踹开车门翻滚而出,凭借过硬的战术规避动作躲过毒贩的扫射,
冷静据枪,一枪精准命中毒贩车辆轮胎,成功逼停。
随后又带伤配合战友制服了试图引爆手雷的亡命徒。两次嘉奖,
一次表彰其临危不惧的勇气和战术素养,
一次表彰其关键时刻挽救战友生命的英勇行为他扑倒了那个差点被手雷波及的新兵。
班长张猛,这个像兄长一样的老侦察兵,早已看穿山子平静外表下翻涌的岩浆。
他欣赏山子的坚韧和勇敢,却也忧心忡忡。一次夜哨,张猛递给山子一根烟:“山子,
你是个好兵,顶尖的好兵。但记住,咱们这身军装,枪口永远只能对外,对着真正的敌人。
心里的鬼…得靠别的法子驱。” 山子沉默地抽烟,火星在黑暗中明灭,
映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眸。张猛退伍前,特意找到山子,塞给他一本崭新的《刑法》,
封皮是庄严的国徽。“带着它,”张猛用力拍着山子的肩膀,“比带着你那块破钢片强!
仇恨是口枯井,你填多少眼泪、多少血,都漫不出来!法律是尺子,是规矩!
别让那点‘恨’蒙了眼,毁了你这把好刀!” 山子接过书,指尖抚过冰冷的国徽,
又下意识摸了摸贴身藏着的、磨得异常锋利的弹簧钢片。钢片的冷硬隔着衣服传来,
像一块无法融化的寒冰。山子在连队是出了名的“哑巴尖刀”。除了必要的报告和命令,
他几乎不说话。但每一次任务,他的行动都像手术刀般精准、致命。
这种沉默的爆发力和对“目标”的绝对专注,让他在战友中是可靠的堡垒,
却也隐隐透着一丝令人不安的偏执。他拆弹时的极致冷静,射击时的绝对稳定,
格斗时那瞬间爆发的、近乎本能的凶狠……这些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的特质,
像一根根被拉紧的弦,绷在他灵魂深处。山子胸前挂上了闪亮的军功章,
臂膀上是象征荣誉的“侦察兵尖子”臂章。他站在军容镜前,镜中的军人挺拔、刚毅,
眼神锐利如鹰。三年的熔炉淬炼,他早已褪去少年的青涩,锻成了真正的钢铁。
战友们敬佩他,连长器重他,他仿佛找到了新的归宿和荣耀。只有他自己知道,
每当夜深人静,抚摸着那本从未翻开过的《刑法》和贴身藏着的冰冷钢片,
镜中军人的眼底深处,那簇名为复仇的幽蓝火焰,从未熄灭,只是在军功章的辉光下,
在钢铁纪律的压制下,燃烧得更加隐秘,更加冰冷,
等待着那个必将到来的、风雪交加的年夜。2005年深秋,
山子的退伍报告压在侦察连指导员的案头,像一块沉甸甸的墓碑。“陈小山!你想清楚!
”指导员拍着桌子,痛心疾首,“提干的命令马上就下来了!你是尖子,是功臣!
部队需要你这样的兵!留下来,前途无量!”窗外,训练场上的喊杀声震天动地,
那是山子流过血汗的地方。山子站得笔直,军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眼神却像越过指导员,
落在窗外遥远而灰暗的秦巴山脉。“报告指导员,”他的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
“家里…有未了的事。必须回去。” 他用了“事”,而不是“心愿”或“仇”。
这个词像一颗冰冷的子弹,堵住了指导员所有挽留的话。张猛临走前的忧虑,
此刻在指导员心头翻涌——那把藏在军功章下的“刀”,终究要出鞘了。退伍仪式上,
山子卸下肩章领花,动作一丝不苟,如同拆卸一件精密武器。他拒绝了战友们喧闹的送行酒,
只在营区门口,对着飘扬的军旗,敬了最后一个标准的军礼。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一道孤绝的刀锋。背包里,那本崭新的《刑法》被压在底层,上面是几枚沉甸甸的军功章,
最上面,盖着那本磨破了边的退伍证。贴身的口袋里,那块来自五金厂的弹簧钢片,
边缘已被摩挲得异常锋利,冰凉的触感贴着心口,像一块永不融化的寒冰。腊月廿八,
黑水沟村。风雪比往年更烈。山子穿着便装,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军用背包,
踩在熟悉的、却无比陌生的山路上。王家那座白瓷砖小楼依旧刺目,
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面包车,车身上喷着醒目的红字——“振峰农家乐·年夜饭火热预订中!
” 村口小卖部的电视里,正播放着本地新闻:“…返乡创业模范王振,浪子回头金不换,
带领乡亲共同致富…” 画面里,王振穿着皮夹克,油光满面地接受采访,
对着镜头侃侃而谈:“…过去年轻气盛犯过错,感谢政府教育改造,
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山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指在口袋里轻轻捻着那块钢片。
冰冷的金属边缘划过指腹,带来一丝锐利的痛感。很好,目标确认,状态良好。他没有回家。
父亲两年前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临死前抓着他的手,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王家方向,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真正的家,
只剩下山梁上那两座孤零零的坟茔。山子径直去了镇上。目标明确,如同执行任务前的侦察。
他花了一天时间,在“振峰农家乐”对面的小茶馆里,像一个普通的外乡客人。
目光透过氤氲的热气,
规律王振、王宝田、王振妻子、帮工、监控死角后院厨房的窗户对着一条僻静小巷。
他走进镇农贸市场最角落的肉铺,目光扫过挂着的刀具。“老板,要两把剁骨刀,厚实点的。
” 声音平淡无奇。他拿起刀,掂了掂分量,指腹划过刀锋,
感受着钢材的硬度和开刃的角度。如同在部队挑选趁手的装备。付钱,
用准备好的旧报纸仔细包好,塞进背包。他避开大路,沿着山脊绕行,
在傍晚风雪最大的时候回到村子。利用地形和天气掩护,如同当年边境渗透。
他选择从后山接近王家,那里积雪深厚,人迹罕至,能完美掩盖足迹。居高临下,
农家乐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正是年夜饭的高潮。2005年腊月廿九,除夕夜,
21:15。风雪成了最好的掩护。山子像一道融入夜色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滑下后山坡,
精准地落在王家后院厨房的窗外。窗户插销是老式的,
他摸出那块随身多年的弹簧钢片——五金厂里打磨出的手艺,
侦察兵掌握的开锁技巧——钢片探入缝隙,轻轻一拨。“咔哒。
”细微的声响被淹没在屋内的喧嚣和屋外的风声中。他推开窗户,敏捷地翻入温暖的厨房,
如同无数次演习中潜入敌后。案板上堆满待切的熟食,灶上炖着肉汤,香气扑鼻。
这温馨的景象与他心中冰冷的杀意形成残酷的对比。他抽出报纸包裹的剁骨刀。
冰冷的刀柄入手,瞬间激活了肌肉深处的记忆。格斗训练的本能接管了身体,心跳平稳,
呼吸悠长,所有情绪被压缩进一个冰冷的点。他拉开厨房通往堂屋的门。
暖黄的灯光、喧闹的劝酒声、电视里春晚的歌舞,扑面而来。王振正背对着门,举着酒杯,
唾沫横飞:“…喝!都他妈给老子喝!今天高兴!
当年那点破事儿算个球…” 同桌的王宝田和几个亲戚笑得满脸通红。山子的出现,
如同寒流瞬间冻结了屋内的空气。所有声音戛然而止。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