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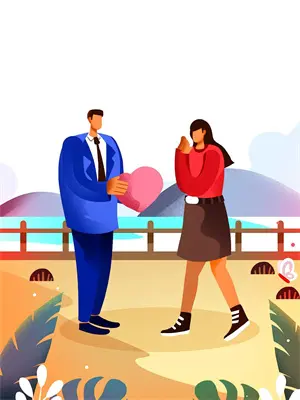
其它小说连载
主角是苏文屈小小的其它小说《一针刺青工作室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其它小作者“余生不相聚”所主要讲述的是:江南的总带着股缠绵的湿淅淅沥缠缠绵像是永远也下不雨丝斜斜地织将整个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青石板路被浸润得油倒映着沿街店铺的幌影影绰看不真屈小小的“一针绣坊”就开在这条巷子门面不却收拾得雅临街的窗棂擦得一尘不窗台上摆着两盆茉叶片上滚着晶莹的雨在雨雾里透着点怯生生的她坐在窗前的梨花木桌桌上铺着块素白的绢针尖在帕上游...
主角:苏文,屈小小 更新:2025-10-15 21:17:32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江南的雨,总带着股缠绵的湿意,淅淅沥沥,缠缠绵绵,像是永远也下不完。
雨丝斜斜地织着,将整个苏州城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里,青石板路被浸润得油亮,
倒映着沿街店铺的幌子,影影绰绰,看不真切。屈小小的“一针绣坊”就开在这条巷子里,
门面不大,却收拾得雅致。临街的窗棂擦得一尘不染,窗台上摆着两盆茉莉,
叶片上滚着晶莹的雨珠,在雨雾里透着点怯生生的白。她坐在窗前的梨花木桌旁,
桌上铺着块素白的绢帕,针尖在帕上游走,绣出半朵并蒂莲的轮廓。那根银针比发丝还要细,
在她指间灵活得像有了生命。她拈针的手法很特别,食指微屈,拇指轻轻抵住针尾,
手腕转动间,丝线便顺着针脚漫延开来,从浅粉到绯红,过渡得自然又细腻,
竟比院角那缸新开的荷花还要鲜活几分。针脚密得像初春的蛛网,细密却不杂乱,
每一针都落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仿佛早就在帕子上画好了无形的线。“姑娘,
这帕子绣得真绝!”门口传来个粗哑的声音,挑着货担的老汉探进半个身子,
黝黑的脸上堆着憨厚的笑,眼睛瞪得溜圆,“莫说苏州城,就是宫里的绣娘,
怕也赶不上您这手艺。您看这颜色,跟刚摘下来的荷花似的,透着水灵劲儿!
”屈小小没抬头,唇角却不易察觉地弯了弯,露出个浅浅的梨涡。
她的绣品在苏州城早就出了名,不是因为花样有多新奇,
而是针脚里藏着旁人瞧不出的门道——就像此刻,她绣莲茎的线看似松散,
实则每三寸就藏着个巧妙的回环,若是用内力猛地一扯,
那些松散的线便能瞬间绷成坚韧的索,比寻常的麻绳还要结实。这手艺是师父传的。十年前,
师父在巷口捡回快饿死的她时,身上就带着股淡淡的药味。师父是个瞎眼老妪,
眼睛上蒙着块青布,却总能准确地摸到她的手,教她如何穿针,
如何让丝线在绢帕上“走路”。“针是有性子的,”老妪的声音总是慢悠悠的,带着点沙哑,
“你待它柔,它便给你绣出花来;你待它刚,它也能替你挡下刀子。”那时她不懂,
只当是师父哄她的话。直到有一次,巷子里的无赖抢她刚绣好的荷包,师父突然出手,
手里那根绣线像长了眼睛,缠住无赖的手腕,轻轻一拉,无赖便疼得嗷嗷叫。她这才知道,
师父教的不只是刺绣。临终前,老妪躺在吱呀作响的竹床上,枯瘦的手紧紧攥着她的手,
掌心的温度比冰还凉。她塞给她个油布包,布面磨得发毛,边角都起了卷。
“若遇戴玉扳指的黑衣人,就把这东西交出去,”老妪的声音气若游丝,
青布下的眼珠浑浊地动了动,像是在努力看清她的脸,“莫多问……切记,
莫多问……”话没说完,那只手便垂了下去。屈小小抱着油布包哭了三天,
后来才敢打开——里面是个巴掌大的锦盒,红绒衬底,躺着根金针,针尾镶着粒圆润的珍珠,
看着倒像姑娘家的饰物,谁能想到,这竟是师父藏了一辈子的东西。雨渐渐停了,
巷口的积水里映出天光,亮得有些晃眼。突然传来一阵笃笃的马蹄声,
敲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清脆又急促,带着股生人勿近的冷意,一点点逼近。
屈小小捏着银针的手猛地一顿,针尖在绢帕上戳出个小小的破洞。她抬起头,透过窗棂望去,
只见个穿玄衣的汉子站在坊门口,身形挺拔,腰间佩着柄弯刀,
刀鞘上的铜环在水光里闪着冷光。最惹眼的是他左手拇指上那枚墨玉扳指,深不见底的黑,
像凝住的夜色。汉子的目光扫过坊内,没有停留墙上挂着的绣品,也没看窗台上的茉莉,
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她,眼神锐利得像刀,仿佛要把她从里到外看个通透。
屈小小的心“咯噔”一下,指尖的银针差点戳到手上。
她认出了那枚墨玉扳指——师父临终前说的,不就是这个吗?汉子迈步进了绣坊,
带起一阵关外的风沙气,混着雨水的湿冷,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他开口时,
声音低沉得像磨过的砂石:“老夫人让我来取样东西。”屈小小捏紧了手里的绢帕,
帕角的丝线被她绞出几道细痕,指节泛白。她强压着心头的慌,
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客官要什么?”汉子没说话,从怀里掏出块玉佩,玉色温润,
上面刻着半朵莲,花瓣的弧度刚刚好。屈小小下意识地摸向袖口,
那里藏着师父给她的另一半玉佩。她慢慢掏出来,两块玉佩一合,严丝合缝,
正好拼成一朵完整的并蒂莲,莲心的纹路都对得丝毫不差。确认无误,汉子才点头,
示意她拿东西。屈小小深吸一口气,走到里屋的柜子前,打开最底层的抽屉,
拿出那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锦盒。油布磨得发亮,她一层层揭开,露出里面红绒衬着的金针,
珍珠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汉子接过锦盒,指尖刚碰到盒盖,还没来得及打开,
巷口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地由远及近,还夹杂着铁器碰撞的脆响,
刺耳得像要划破这雨后的宁静。汉子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神里闪过一丝厉色。
他迅速把锦盒塞回屈小小手里,力道大得有些硌人:“收好!往城西破庙去,有人等你!
”话音未落,他已拔刀冲出绣坊,弯刀“唰”地出鞘,寒光一闪,
劈在巷口冲来的几个黑衣人身上。那些黑衣人穿着夜行衣,脸上蒙着黑布,
手里的钢刀在光线下闪着凶光。“哐当!”刀剑相击的脆响炸开在巷子里,
混着黑衣人的怒喝和玄衣汉子的闷哼。屈小小抓起锦盒,紧紧抱在怀里,那盒子烫得像团火,
灼烧着她的掌心。她知道,师父没说错,这针果然是要命的东西。她咬了咬牙,
转身从后窗翻了出去。窗台上的茉莉被碰掉了几片叶子,落在湿滑的地面上。
她踩着墙根的青苔往巷尾跑,鞋底沾着的泥水甩在裙摆上,凉丝丝的。
身后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玄衣汉子的闷哼声一次比一次重,像锤子敲在她的心上。
跑过石桥时,她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绣坊的方向已经腾起股黑烟,
滚滚地冲上灰蒙蒙的天,像朵沉甸甸的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
那间她绣了无数个日夜的小坊,此刻怕是已经成了火海。雨又开始下了,淅淅沥沥,
打湿了她的头发和衣衫。屈小小把锦盒抱得更紧了,仿佛那不是一根金针,
而是师父沉甸甸的嘱托,是玄衣汉子用命护着的东西。她不知道城西破庙里等着她的是谁,
也不知道这根金针藏着什么秘密,只知道师父让她交出去,玄衣汉子让她活下去。
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前路被雨雾笼罩,看不真切。但她攥紧了锦盒,一步步往前跑,
溅起的水花打在裤脚,冰凉刺骨,却让她清醒得很——从今天起,她的绣针,
怕是再不能只绣荷花了。城西的破庙早没了屋顶,只剩半截残碑立在齐腰深的荒草里,
碑上“观音庙”三个字被风雨啃得只剩个模糊的轮廓,风一吹,草叶“沙沙”作响,
倒像有人在碑后磨牙。屈小小缩在供桌后,怀里的锦盒棱角硌着肋骨,
疼得她喘不过气——那盒子里的金针像团火,烫得她手心冒汗,却又不敢松手,仿佛一松,
师父和玄衣汉子的性命就会跟着碎掉。日头往西山沉,把天染成了血红色,
庙里的阴影被拉得老长,像无数只手在地上爬。屈小小盯着庙门,耳朵竖得像兔子,
听着外面的动静。供桌是用整块老松木做的,积着厚厚的灰,她指尖蹭过桌面,
摸到道深深的刻痕,像把剑劈出来的。“窸窸窣窣——”脚步声从远处飘来,
轻得像猫爪踩在枯叶上,一下下挠在人心尖上。屈小小屏住气,手往袖管里缩,
指尖触到那根银针——师父临终前塞给她的,针尾淬了麻药,针身细得能藏在发髻里,
平时绣花都嫌软,此刻却硬得像块铁。庙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夕阳的金光裹着个人影挤进来。是个穿蓝布衫的书生,手里摇着把折扇,
扇面上画着几笔淡墨山水,看着倒像来游山玩水的。他眉眼清俊,嘴角噙着笑,
看见供桌后的屈小小,愣了愣,随即拱手作揖,声音里带着股书卷气:“姑娘也是来避雨的?
看这天色,怕是要下晚雨了。”屈小小没作声,只盯着他的鞋。书生的鞋面上沾着泥,
却半点青苔都没有——庙外石阶长满了滑溜溜的青苔,寻常人走进来,鞋底难免沾几片,
他倒像踩着云过来的。再看他的手,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干净,可虎口处那层薄茧,
深得像刻上去的——那是常年握剑的人才有的痕迹。“在下苏文,”书生没等她回应,
自顾自坐在块断砖上,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来,里面是几块桂花糕,油光发亮,
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姑娘若是饿了,尝尝?这是玄妙观的点心,甜而不腻,今早刚买的。
”屈小小指尖的银针已滑到掌心,针尾抵着掌心的肉,扎得有点疼。她盯着苏文,
看他慢悠悠地拿起块桂花糕,却不吃,只放在鼻尖嗅了嗅,眼神往庙门瞟了瞟,
像是在等什么。突然,庙外刮起阵狂风,卷着草叶扑进门,吹得残碑后的荒草“沙沙”乱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里钻,窸窣声越来越近,带着股腥气——不是野兽的腥,
是汗臭混着铁锈的味。苏文的折扇“唰”地合上,捏在手里,眼神瞬间冷了,
刚才那点书卷气荡然无存,像换了个人:“来了。”话音刚落,庙门“哐当”被撞开,
七个黑衣人涌了进来,手里的钢刀在夕阳下闪着寒光,刀刃上还沾着泥,
像是刚从地里刨出来的。为首的是个独眼龙,脸上有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疤,红肉翻着,
看着像条蠕动的蜈蚣。他看见屈小小,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笑,
像破风箱在响:“把金针交出来,饶你个全尸!”屈小小往苏文身后缩了缩,
指尖的银针捏得更紧。苏文往前一步,挡在她身前,折扇“咔”地一声,
竟从中间弹出根细剑,剑身上缠着银丝,在光线下泛着冷光,像条冻住的蛇:“就凭你们?
”独眼龙狞笑一声,挥手道:“给我上!抓活的!”黑衣人一拥而上,钢刀劈得“呼呼”响。
苏文的细剑突然动了,快得像闪电,银光在刀影里穿来穿去,每一剑都挑在黑衣人的手腕上。
屈小小看得眼花缭乱,只见他左脚点地,右脚腾空,细剑顺着对方的刀身滑上去,
“噌”地挑掉人家的刀,反手一掌拍在胸口——那黑衣人像个破麻袋,倒飞出去,
撞在残碑上,哼都没哼一声。“好身手!”屈小小心里暗赞,突然想起师父说过,
真正的高手,杀人不用蛮力,就像刺绣,得找对针脚的缝隙,一针挑断线头,
整朵花都能散架。可黑衣人实在太多,倒下一个,又冲上来两个。苏文渐渐落了下风,
额角渗出汗珠,细剑的银光慢了些。一个矮个子黑衣人瞅准空当,绕到苏文身后,
钢刀带着风声劈过来。屈小小脑子一片空白,
只记得师父教的“急中针”——指尖的银针猛地扬出去,不是扎人,是用巧劲往刀背上弹。
银针带着风声,“叮”地撞在钢刀侧面,那刀顿了顿,劈偏了寸许,擦着苏文的肩头过去,
带起片血花。“好手法!”苏文趁机回身,细剑穿胸而过,矮个子黑衣人眼睛瞪得溜圆,
倒在地上。他回头看了屈小小一眼,眼里闪过丝惊讶,随即又沉下脸,对付剩下的人。
独眼龙见状,突然从怀里掏出个铁哨,“呜——”地吹了声,哨音又尖又利,
像指甲刮过玻璃。庙外立刻传来马蹄声,“哒哒哒”越来越近,还夹杂着人喊马嘶,
听着至少有十几人。独眼龙狞笑着后退,退到庙门口:“给我搜!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金针!
找不到就把这庙烧了,我看她出不出来!”苏文拽了屈小小一把:“走!
”他拉着她往庙后跑,那里有个被荒草盖住的狗洞,洞口只比水桶粗点。苏文先钻了出去,
回头伸手:“快!”屈小小咬着牙,趴在地上,拼命往洞里挤。洞壁的土刮得胳膊生疼,
她听见身后黑衣人的吼声:“在那儿!别让他们跑了!”钢刀砍在供桌上,木屑飞溅。
钻出狗洞,才发现外面是片密不透风的树林,藤蔓缠在树上,像无数条绳子。
苏文拉着她往林深处跑,屈小小跟不上,几次差点被藤蔓绊倒。跑了约莫半个时辰,
直到听不见身后的动静,两人才靠在树干上喘气。月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
照在苏文的细剑上,血珠顺着剑刃往下滴,落在草叶上,像串碎红宝石。他抹了把脸,
汗混着血,在脸上冲出两道印子。“你知道那金针是什么吗?”苏文突然开口,
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树林听见。屈小小摇头,心脏还在砰砰跳,
刚才那一刀擦着苏文肩头过去时,她吓得差点停了呼吸。“那是‘绣春刀’的兵符。
”苏文的声音里带着股寒意,“三十年前,先帝派绣春卫暗查藩王谋反,
领头的指挥使用金针作信物,号令手下。后来事情败露,绣春卫被藩王灭口,
只剩指挥使的夫人带着金针逃出来——就是你师父,对不对?”屈小小的心猛地一沉。
师父瞎掉的眼睛、布满老茧的手、总在夜里摸出的旧令牌……那些她从没细想的细节,
突然串成了线。难怪师父总说“针能杀人,也能救命”,难怪她绣的护身结,
骨子里都藏着剑的形状。“你师父不说,是怕你卷进来。”苏文看着她,
“藩王的人找了这金针三十年,找到它,就能顺藤摸瓜,把剩下的绣春卫一网打尽。
”屈小小摸了摸怀里的锦盒,金针隔着布都在发烫,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钻出来。
她突然想起师父临终前的样子,老妪躺在床上,青布蒙着的眼睛里,
似乎有泪渗出来:“别恨我……让你学绣,是想你离刀远些……”原来那些年绣的并蒂莲,
针脚里藏的都是暗号;那些磨得发亮的绣线,早就浸过了麻药;那些看似柔弱的花花草草,
骨子里都是杀人的招式。她以为自己学的是刺绣,其实学的是保命的本事。“那你是谁?
”屈小小抬头问苏文,月光照在他脸上,才发现他眉骨处有道浅疤,平时被头发挡着看不见。
苏文沉默了会儿,从怀里掏出块玉佩,玉佩上刻着半只鹰:“我爹是绣春卫的百户,
当年被藩王的人杀了。我找这金针,是为了替我爹报仇。”屈小小愣住了。
她看着怀里的锦盒,突然明白师父为什么要把金针交给她——不是让她藏,是让她用。
就像师父教她的,针既能绣出繁花,也能挑断筋骨。“他们还会追来吗?”屈小小问,
声音有点抖。苏文点头,握紧了细剑:“独眼龙是藩王手下的‘血煞卫’,最是阴狠。
今晚怕是睡不成了。”话音刚落,远处传来几声狼嚎,不是真狼,
是人在学狼叫——那是血煞卫的暗号,用来报信。苏文拽起屈小小:“走!往山顶跑,
那里有我们的人。”两人又开始跑,月光在前头引路,身后的狼嚎越来越近。
屈小小攥着锦盒,指节发白,她知道,从钻出狗洞的那一刻起,她手里的针,
就再也绣不出纯粹的花了。那些藏在针脚里的杀机,终究要见血的。
客栈的油灯芯子“噼啪”爆了个火星,把屈小小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像个跳动的鬼魅。她把那根金针平放在八仙桌上,指尖沾了点唾沫,
轻轻捻着针尾的珍珠——这珍珠是师父用鱼鳔胶黏上去的,平时看着就像个普通的装饰品,
此刻摸上去,才觉出珍珠边缘有道极细的缝,像片被虫蛀过的叶子。“我来试试。
”苏文凑过来,他的指尖还带着细剑的寒气,捏住珍珠轻轻一旋,只听“咔嗒”声,
珍珠竟像螺帽似的转了下来,露出针尾的空心管,
里面果然塞着东西——卷得像根棉线似的绢纸,展开来也只有指甲盖大,
上面的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是用胭脂调了明矾写的,遇热才显形。屈小小赶紧端过油灯,
把绢纸凑到火苗上烘。原本空白的纸上,渐渐浮现出淡粉色的字迹,
像花苞慢慢绽开:“玄武湖畔,三台阁,初七,见水纹。”字是簪花小楷,笔锋柔中带刚,
正是师父的笔迹。屈小小鼻尖一酸——师父总说自己手笨,绣不出细字,
原来她的字藏得这么深。“水纹?”苏文皱起眉,“玄武湖的水纹每天都在变,这是啥暗号?
”他拿起金针对着光看,突然“咦”了一声,“你看针身的花纹,不是缠枝莲,是鱼鳞!
”屈小小凑近了才看清,那些看似花瓣的纹路,放大了看竟是层层叠叠的鱼鳞,
每片鱼鳞上都刻着个小点,顺着针身排列,正好是七组。
她想起师父教她认时辰的法子:“师父说过,初七是‘水神诞’,湖水会涨潮三次,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