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趣游话外 > > 《梧桐之下,她入镜时》(周叙白老陈)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热门小说《梧桐之下,她入镜时》周叙白老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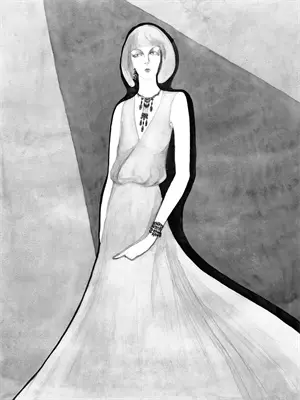
都市小说连载
“墨殇缘浅”的倾心著作,周叙白老陈是小说中的主角,内容概括:故事主线围绕老陈,周叙白,沈知意展开的现实情感,先虐后甜小说《《梧桐之下,她入镜时》》,由知名作家“墨殇缘浅”执笔,情节跌宕起伏,本站无弹窗,欢迎阅读!本书共计11135字,1章节,更新日期为2025-09-24 06:08:59。该作品目前在本网 sjyso.com上完结。小说详情介绍:《梧桐之下,她入镜时》
主角:周叙白,老陈 更新:2025-09-24 06:34:17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第一章:她站在春天里南京的春天,是从一阵风开始的,风先掠过紫金山巅,
再穿过玄武湖面,最后停在鸡鸣寺路的樱花枝头,颤巍巍地摇落一树粉白。花瓣簌簌落下,
像一场迟来的春雪,铺满了青石板路。阳光从梧桐枝叶的缝隙里漏下来,
在地上切出斑驳的光影。周叙白站在树下,手里那台老式胶片相机已经磨出了铜色的边角,
快门键上那道浅痕是林晚留下来的。他没戴手套,指尖冻得发红,却稳稳托着相机,
像是在等待什么。这已经是他第七年来鸡鸣寺拍樱花了。从前总是和林晚一起,
她爱穿米白色风衣,站在树下安安静静地望着他,等他按下快门。他常说“你比樱花好看”,
她总是摇头:“花会谢,但光能活很久。”后来她走了,
在那个暴雨初起的凌晨一辆失控的货车,一条没发完的短信:“我在路上,樱花快开了。
”之后整整一年,他没碰过相机。直到去年春天,他才重新从抽屉里取出它,
像拾起一段不敢触碰的回忆。今天,他不是来拍樱花的……快门轻响,他拍了一棵梧桐,
树干上刻着模糊的字迹像是“等你”,不知道是谁刻的,也不知道在等谁。
他拍它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那像某种隐喻,在时间冲刷下依然固执地留下痕迹。就在这时,
他看见了一个姑娘。她站在樱花雨里,穿浅灰色羊绒大衣,长发被风轻轻撩起,
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她没有打伞,也不像旁人那样兴奋地拍照,
只是静静望着最老的那棵樱花树,眼里有种说不清的沉静。周叙白的手指停在快门上,
迟疑了一秒,然后按了下去。咔嚓。那声轻响像一道闪电,
突然劈亮了他心里某个蒙尘的角落,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站在这里,
但他莫名觉得她不该只是个路人。她像是从某段被遗忘的时光里走出来的人,站在春光里,
站在他镜头的正中央。她忽然侧过头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视线,
目光轻轻扫过人群最后落在他身上,周叙白没有躲开。他只是静静看着她,
像在看一个早就该遇见的人,她没有笑也没有走近,
只抬手将一缕碎发别到耳后然后转身走进樱花深处,背影渐渐被花雨吞没。
周叙白低头看向相机,那张照片还没显影,但他知道—她已经入镜了,不是风景,不是过客,
是某种即将开始的什么。他走出树影,踏着落花的石板路,朝她消失的方向走去,风又起了,
樱花如雨,头顶梧桐叶沙沙作响,像低语又像见证。……而此时的城市另一端,
沈知意正站在南京大学老图书馆的露台上,望着鸡鸣寺的方向。她手里攥着一份设计图,
标题写着:“老城南记忆馆——设计方案”。她不知道,自己刚刚成了别人照片里的主角,
更不知道—这张照片将会改变两座建筑的命运。一座是她倾注心血设计的记忆馆,另一座,
是她从未对人言说的心。沈知意不是南京人,却比许多本地人更懂得这座城,
她的父亲是建筑修复师,母亲教历史。童年最深的记忆,是父亲在中山陵廊柱下测量裂缝,
母亲在明城墙砖石间拓印铭文,她从小就知道建筑不只是石头,更是盛放时间的容器。
三年前,她从剑桥回来,放弃了伦敦事务所的offer,
执意回南京参与“老城南更新计划”。她想做的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记忆继续活下去,
她设计的“记忆馆”,以老宅院为基,用玻璃和钢构架起透明穹顶,像一本打开的书,
嵌进历史的缝隙。她希望人们走进这里,不只是看展,更能听见时光的回响,
可方案提交三个月石沉大海。今天她站在露台上,
手里攥着刚刚收到的消息:“赵世荣的开发集团已接手老城南地块,原规划或将全面推翻。
”赵世荣,南京地产界有名的“推土机”,只讲效益,不谈旧情。她闭上眼,
风从秦淮河吹来,带着水汽和梧桐叶的清香。“如果连记忆都要被拆掉,我们还剩下什么?
”她轻声问。没有人回答。只有远处钟声传来,不知是鸡鸣寺的钟响,还是记忆深处的回音。
……周叙白回到云栖公寓时,天已经擦黑,他住在五楼,不到五十平的老单元房。
墙上贴满了照片:梧桐、旧巷、石桥、老人……全是南京城“即将消失的角落”。
他管这些叫“城市的遗照”。他取出胶卷走进暗房,红灯亮起,显影液在玻璃槽中轻轻荡漾,
胶片缓缓浸入液体像在进行一场沉默的仪式。
的背影、阿婆李煮糖芋苗的灶台、小满在图书馆看书的侧脸—还有一张樱花树下的陌生女人。
他把她的照片单独取出贴在墙面最亮的地方,她站在春天里,
风拂发梢眼神沉静像在等待一个答案。他看了很久,最后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敲打着玻璃,像在低语。夜深时,
周叙白从书架深处摸出一个生锈的铁盒,锁扣已经坏了,打开来,里面是一本皮面笔记本,
边角磨损,纸页泛黄。封面上写着:“林晚的南京手记”。他翻开第一页,
是她的字迹:“南京的梧桐是会说话的,它们记得所有发生过的事。”他合上日记,
指尖轻轻抚过封面。窗外月光洒在梧桐叶上,像落了一场无声的雪。
第二章:弯腰的清晨凌晨四点三十七分,南京的天色还沉着,老陈已经醒了,
他住在城南一条老巷深处,屋子不足三十平,墙皮有些剥落,天花板上悬着一盏老式白炽灯,
灯罩蒙着灰。床头摆着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收着三张照片:一张是他和妻子在夫子庙的合影,
一张是儿子小学毕业时的笑脸,还有一张,是空的—相框还在,照片却不知何时不见了。
他没开灯,怕吵醒隔壁租住的年轻人。摸黑起身,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橙色工作服,
弯腰系好鞋带,又从抽屉里取出一副旧棉手套—指头处已经磨破,他却始终舍不得扔。
他常说:“手套是手的皮,手是扫帚的根。”五点整,他推着清洁车出门。
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像一首重复了二十年的晨曲。
巷子两旁是老式民居,马头墙高低错落,瓦楞间生着青苔,偶有早起的老人推开木门,
见是他便点点头:“老陈,早啊。”他也回一句:“早,您慢点走。
”他负责从中华门到长乐路这一段,整整两公里,这段路他扫了二十年。二十年前,
他从苏北农村来南京打工,妻子病重,儿子刚上小学。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在工地守过夜,
最后才进了环卫队,起初觉得难为情怕遇见熟人,后来却渐渐觉得城市干净了,人心才安稳。
他扫地从来不赶,每一片落叶、每一团纸屑、每一截烟头,他都俯身拾起,轻轻放入簸箕。
有人笑他:“老陈,你这不是扫地,是绣花呢。”他只笑笑:“地干净了,人走着才安心。
”清晨六点,天光微亮,他走到中华门城堡下,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烟,
抽出一根点上。火光在朦胧中一闪,像一粒微弱的星,他望着城墙沉默的轮廓,
轻声说:“老伙计,又见面了。”这城墙他扫了二十年,每一块砖他都熟悉,
有些砖上刻着“南京造”的字样,有些被风雨磨去了名字。他曾听游客说:“这些砖,
是明朝人一块块砌起来的。”他没说话,只是蹲下身用手指抚过砖缝,
那里面像藏着六百年的风。他继续往前,路过一家刚开门的早点铺,老板娘瞧见他,
端出一碗热豆浆:“老陈,喝一口暖暖。”他摆手:“刚抽过烟,嘴苦。
”老板娘执意递过来:“喝吧,你扫我门口三年了,这碗是谢你的。”他接过,小口喝着,
热气扑在脸上,像一种无声的安慰,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那个女孩。
她蹲在路边手握一个玻璃瓶,正小心翼翼地将落在地上的樱花花瓣拾进去,花瓣沾着晨露,
她动作极轻,像在收集什么易碎的念想。老陈停下扫帚,在不远处静静看着,
女孩穿素色棉布裙,头发扎成低马尾,脚上一双布鞋,鞋尖已有些磨损。她把花瓣装好,
又从包里取出一张纸条,写了几行字,塞进瓶里,轻轻盖上木塞。她站起身,看见老陈,
微微一怔,随后笑了:“叔叔,我在做春天的信。”老陈点点头:“好看。
”“我想把春天寄给一个朋友,”她轻声说,“她走的匆忙,没看到樱花。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干净的小塑料袋,递给她:“用这个装,
不容易返潮。”女孩接过来,眼睛亮了一下:“谢谢您。”她将花瓣重新装进袋子,
又在纸条上加了一句:“今天有位扫地的叔叔,给了我一个袋子。”老陈没说话,继续扫地,
只是这一次,他俯身的动作比平时更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女孩离开后,
他走到她刚才蹲过的地方,发现地上留着一张小纸片,是她写剩的草稿,
上面写着:“春天年年都会回来,而你不会。但我还是想让你看看,今年的樱花。
”他把纸片拾起,放进清洁车的工具箱里,和那只空相框放在一起。……老陈本名陈建国,
东北人,二十年前,妻子因尿毒症去世,欠下十几万债,他带着儿子来南京想寻一条活路,
可工地没干几年,腰就坏了,只好转做环卫。最难的时候,
儿子在学校被同学笑:“你爸是扫垃圾的。”儿子回家哭,他没说话,
第二天却带儿子一起上街,看他扫地。“你看,”他说,“这条街,昨天还脏,
今天就干净了。人也一样,只要肯弯腰,就能把日子扫亮。”后来儿子考上大学,去了上海,
临走前说:“爸,我以后给你买新房子。”他摇头:“我不走,就住这儿,
这城南的路我扫惯了。”他不是没想过退休,可每次递交申请看见新来的年轻人扫得马虎,
他又忍不住拿回扫帚。“有些事,”他说,“不是钱的事。”……七点二十三分,
阳光终于穿过梧桐叶,落在南京大学老图书馆的台阶上。沈知意提前半小时到,
今天她要参加“老城南更新项目”的初步评审会,虽然知道希望渺茫。走进会议室,
赵世荣的代表已经到了,一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手持平板脸上没什么表情。“沈设计师,
”对方开口,“赵总的意思很明确:记忆馆概念太‘文艺’,没有商业价值,
我们建议改为高端商业综合体,保留部分外立面内部全部重建。
”沈知意握紧手中的图纸:“那不是重建是拆除,
那些老宅院是几代人的生活痕迹不是装饰品。”“痕迹不能变现,”对方语气冷淡,
“赵总说,南京需要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会议持续四十分钟,最终以“方案暂缓”告终。
沈知意走出大楼,阳光正洒在图书馆的玻璃幕墙上,折射出刺眼的光,
她闭上眼听见远处传来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循声望去,
一个橙色的身影正在梧桐树下缓缓移动。她忽然想起昨晚的梦:自己站在废墟中,
手拿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她设计的记忆馆,门牌上却写着“已拆除”。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有些弯腰的人,比挺直腰的人更接近大地。
”她走向那位扫地的老人:“叔叔,”她轻声问,“您扫这条路多久了?”老陈抬头,
认出是昨天那个拾花瓣的女孩,笑了笑:“二十年了。”“您觉得……这城南的老房子,
该拆吗?”老陈停下扫帚,望向远处的马头墙:“我扫地不是为了拆,是让走路的人安心,
房子也一样,拆了,路就空了,心也就空了。”沈知意怔住了,
她忽然明白她要设计的不是一座馆,而是一种尊严。下午沈知意去图书馆查资料,
在古籍区她遇见小满,一个常来读书的女孩,总坐在靠窗位置,面前摊着一本旧笔记本。
“你在写什么?”沈知意问。小满抬起头,笑了笑:“记录老城南的故事,我奶奶说,
如果没人记得,那些人就真的消失了。”她翻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1953年,
陈师傅在长乐路修车,每天扫门前的路,从不断。”第二页:“1978年,
李阿婆在巷口卖糖芋苗,冬天也热着锅。”第三页:“1993年,
一个环卫工开始扫中华门路段,他叫陈建国。”沈知意蓦地抬头:“这些……是谁告诉你的?
”“我奶奶,”小满说,“她以前住城南,认识很多人。她说,老陈是个好人,
扫地时连蚂蚁都绕着走。”沈知意沉默良久,从包里取出一张纸,画下一座建筑的草图,
她写下标题:“城南记忆馆·致敬每一个弯腰的人”。晚上九点,老陈坐在小屋门前,
听着那台老式收音机,电台正在播天气预报:“明日多云转晴,气温回升,
樱花进入最佳观赏期……”他关掉收音机,抬头望天。月亮很亮,梧桐叶在风中轻轻摇晃,
他从工具箱里取出那个塑料袋,里面是女孩留下的花瓣和纸条,又拿出那只空相框,
将纸条小心地放进去。他不知道那女孩叫什么,也不知道她朋友是谁,
但他知道有些记忆不该被扫走,他轻声自语:“明天,我扫慢一点。
”风穿过巷子像在回应他。第三章:未寄出的信春意渐尽,樱花开始零落,
花瓣轻覆屋檐、石阶、车顶,像一场缓慢而温柔的告别。与此同时,梧桐的新叶悄然舒展,
绿意渐浓,在城市半空晕开一片湿润的夏意,气象台预报,
这个星期将迎来今年第一场真正的夏雨,洗尽春天最后的痕迹。
沈知意坐在老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一叠图纸,她一夜未眠,
桌上散着铅笔屑、干涸的咖啡渍,和几团被揉皱又试图展平的草稿纸,而在所有凌乱之间,
是那张全新的建筑手稿—城南记忆馆·致弯腰的人。她推翻了先前的方案,
不再只是做一个“记忆的容器”,而是营造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新设计以传统宅院为基,
但中庭不再封闭,转而敞开为一座小型广场,
地面以青石板铺出波纹形态象征“被扫过的路”。
广场中央立着一座低矮的铜像:一个弯腰的背影,手握扫帚,
底座刻着一行小字:“有些弯腰的人,比挺直腰的人更接近大地。
”她把老陈的故事写进了设计说明,附上小满笔记本里的片段,
还夹入那个装着樱花花瓣的玻璃瓶照片。“这不是建筑,”她在末尾写道,“是尊严的形状。
我们纪念的并非过去,而是那些无声托起过去的人。”她合上图纸轻轻呼出一口气,
窗外的阳光正斜打在图书馆的玻璃幕墙上,折出七色光影,像一场安静而盛大的庆典。
同一时刻,周叙白正站在暗房里,红色灯光笼罩,空气里弥漫着显影液特有的气味,
他小心地将昨天在鸡鸣寺拍摄的胶片浸入药水中。
相纸渐渐浮现影像:樱花、梧桐、人群……然后,是那个穿灰色大衣的背影。
他放大细节一再调整焦距,就在她转身的刹那镜头的不远处,
一个橙色的身影正俯身扫地是老陈。周叙白怔住了,他从未留意过这位老人,但在胶片上,
老陈的身影格外清晰:微微佝偻,扫帚划过地面,像写下某种无人能读的文字。
阳光从梧桐叶隙漏下,落在他肩上,如一层浅金,他突然想起林晚说过:“最动人的光,
常常不在风景里而在人低头的瞬间。”他冲洗了三张照片:一张是沈知意立于樱雨之中,
一张是老陈弯腰扫地的侧影,第三张,他将两张底片叠印在一起——她与他,
共存于同一片梧桐之下。周叙白将照片夹进随身的牛皮笔记本,写下标题:《未寄出的信》,
他知道有些影像生来不为展示,只为等待一个被真正看见的时刻。……小满坐在电脑前,
手指悬在键盘上久久未落,她打开了本地媒体的投稿页面,
在标题栏缓缓键入:“请留住城南的记忆——一个环卫工与一座城的故事”。
她将奶奶口述的老城南旧事、老陈的日常、沈知意的设计理念,还有那张玻璃瓶的照片,
一一整理成文,她在文末写道:“记忆不是历史的尘埃,而是让城市站起来的土地。
”点击“发送”,屏幕上显示:“投稿成功,将在24小时内审核。”她关掉电脑,
望向窗外,雨还没有来,但风已起了,梧桐叶沙沙作响,如同某种遥远而坚定的回音。
……三天后,市规划局会议室,沈知意站在投影前,对面是赵世荣的团队,
一位穿黑西装的代表冷笑道:“沈设计师,你这是在打感情牌?我们是城市更新,
网友评论
资讯推荐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