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青天白日下沈彦卿被强娶豪夺了。
赵景澜看向面前的女子,面前的女子妆容不是哪种很艳丽,而是一种一种恰到好处的淡雅。
不是那种刻意雕琢的精致,也不是全然素面朝天的寡淡。
她的脸上似乎只薄施脂粉,却掩不住眉宇间的苍白,那苍白在淅淅沥沥的雨声和这略显诡异的 “青天白日” 映衬下,更添了几分脆弱。
眉毛是细细的,顺着原本的眉形略加修饰,并不张扬,却显得干净利落。
眸子是清亮的,此刻却像蒙着一层水雾,带着一丝迷茫,一丝倔强,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 疏离。
那眼神没有看他,而是微微垂着,或是飘向窗外连绵的雨帘,仿佛这满堂的喧嚣和他这个 “新郎”,都与她无关。
唇上是浅淡的胭脂,约莫是豆沙色或是蔷薇色,并不鲜艳,却将她原本略显单薄的唇形勾勒得恰到好处,此刻唇瓣紧紧抿着,像是在无声地抗拒着什么,反而添了几分倔强的楚楚可怜。
整体看来,这妆容就像是水墨画上最淡的那几笔,没有浓墨重彩的冲击,却自有一种清丽脱俗的韵味,如同空谷幽兰,于无声处散发着淡淡的、却不容忽视的芬芳。
它试图营造一种温顺娴静的假象,却偏偏被她眼底那点不屈的星火和紧抿的唇线,泄露了主人真实的心境 —— 那是一种被迫接受安排下的、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赵景澜看着,心中竟莫名地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
这不像一个新娘,倒像一朵在风雨中被迫绽放,却依旧努力维持着风骨的白梅。
沈彦卿微微掀起马车的小窗帘,一股混杂着香烛、小吃和人潮喧闹的热气扑面而来。
她拢了拢身上素雅的衣裙,对着窗外那略显憨厚的马夫点了点头,声音轻柔却清晰:“知道了,王伯。
停在那边柳树下就好,莫要挡了路。”
“欸,好嘞,小姐!”
王伯应了一声,熟练地吆喝着马匹,小心翼翼地将马车停靠在不远处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柳树下。
车外,果然是一派热闹景象。
正值庙会,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各种摊贩的叫卖声、孩童的嬉笑声、杂耍班子的锣鼓声、戏台上传来的咿咿呀呀的唱腔,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生动鲜活的市井交响乐。
空气中弥漫着糖炒栗子的甜香、烤红薯的焦香,还有远处寺庙飘来的淡淡檀香。
沈彦卿待马车停稳,接过王伯递来的小巧竹篮,又叮嘱道:“王伯,我大约一个时辰后回来,您不必等得焦急,可寻个阴凉处歇脚。”
“小姐放心逛,老奴就在这儿守着,丢不了!”
王伯憨厚地笑了笑,露出淳朴的牙齿。
沈彦卿提着篮子,款步走下马车。
她今日并未施粉黛,只着一身月白色的襦裙,裙摆上用银线绣着几枝疏落的兰草,衬得她本就清丽的面容愈发娴静脱俗。
她微微侧头,避开一个奔跑而过的小厮,目光好奇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投向这繁华而喧嚣的庙会深处。
她今日出门,一来是想为病中的母亲求一道平安符,二来,也是想亲自感受一下这久违的人间烟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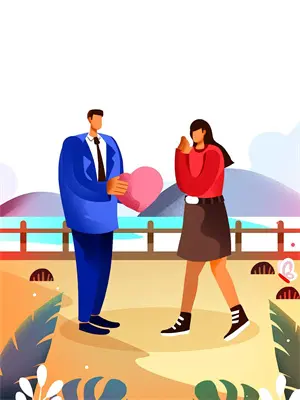
最新评论